| 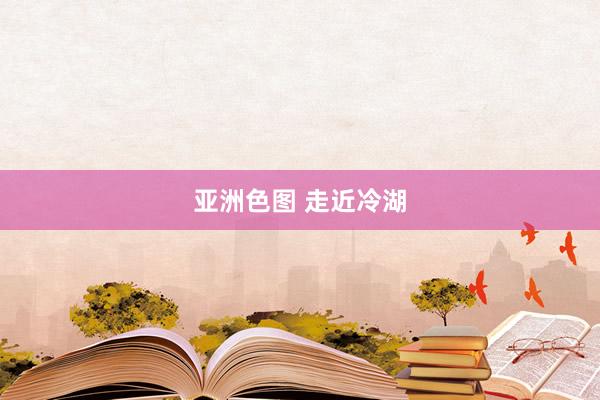
作者:周蓬桦亚洲色图
一地白霜
天蒙蒙亮,咱们起床蛊卦,准备登程。上车前,我刻意瞅了一眼敦煌宾馆院内那一滑银光闪闪的白杨树——咱们此行要去的地点,地上莫得一棵树,天外莫得一只鸟。阿谁地点叫冷湖,是个小镇,位于柴达木盆地的西北角落,曾是青海油田驻地。大当然安排荒凉的地带由风雪居住,由恶劣的表象掌控,却把东谈主类所需要的动力藏于其中。
一齐向西,车窗外的果园和荞麦地隆重消逝,拔帜易帜的是深广的荒野和攻击的远山。当车子停稳,我站在了着实的戈壁滩上,抬眼是随地的卵石,荒芜的梭梭草、骆驼刺,还有大片白茫茫的盐碱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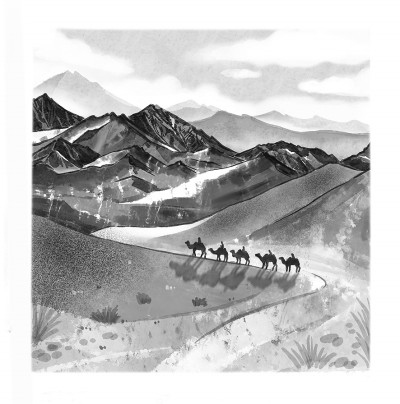
插图:李娜
一个个油田在我的脑海里掠过:玉门、大庆、华北、告捷、蔓延、克拉玛依、塔里木……这些石油工业基地,大多处于冷漠的地域。第一代石油雄兵栉风沐雨、在严酷的环境下办事的场景一幕幕闪现,浓缩为一部石油工业的创业史。关连词,同业的一又友说,就当然环境而言,柴达木盆地是最恶劣的——莫得“之一”。“天上无飞鸟,地上不长草,风吹石头跑,氧气吃不饱。”这是冷湖地貌、环境的果真写真。将这首打油诗拆解开来,每一句王人硌得东谈主心口窝生疼。
一个叫勇子的采油工,永恒陪伴傍边。他是义结金兰的“油二代”,冷湖是他的出身地,他在这里读完初中,之后到茫崖镇上学。那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,第一次见到大片的草和树,他惊喜地抱着一棵白杨哭了起来。
在冷湖,最早的住所是军用帐篷,如今仍是无法设想上万东谈主在沙漠里扎帐篷的场所。自后是地窝子,即一半在地下,一半在大地的住所。上世纪50年代,柴达木连一根柴火王人莫得,青海石油东谈主烧火作念饭全靠原油废渣,一顿饭作念完,脸上布满了灰——最要命的是,易出安全事故。
东谈主们领先用煤油灯照明,自后是电石灯。冬天一到,从地窝子里懒散出一缕缕橘黄色的微光,远眺望去,像是从地下冒出来的火苗。男东谈主喝一口烈酒,就一块咸菜疙瘩、一碗面——这里的水很难烧到怡悦,饭菜作念到八老成就出锅了。女东谈主则在灯下补缀概况的工装,给孩子赶制一对过冬的鞋垫。
多年后,随着国度石油勘测策略东移和冷湖油田原油产量逐年递减,数万名员工及家属西进东迁,冷湖石油基地隆重千里寂,如今已是一派古迹。勇子领着我从一滑排废地中找到了我方小技能的家。屋子由油矿调和计算开导,面积不大,但石油东谈主总算告别了莫得窗户的地窝子。房墙是用黄土加青稞秆和泥而成,这么的屋子和我桑梓鲁西平原上的泥巴屋异常相似。不同的是,咱们房前有浩大的院子,院内院外种着大白菜、胡萝卜、大葱、芫荽等菜蔬,环绕着院子的是爬满梅豆秧的竹篱墙,总会招引成群的蜜蜂飞来。
恰是那一群在生计上不着重的采油东谈主夙兴昧旦,用东谈主力扛油管,背向昆仑,面朝当金山,勘测出一个个锃光瓦亮的大油田。
风静静地吹
我的双脚踩在戈壁滩上,目前是大片绵延攻击的山峦,山头被直快白雪灭绝,常年不化。风静静地吹,我陪伴向导集合一个幽闭之地——盛名的冷湖四号义冢。
这里莫得松柏环绕,只好黄沙相伴。引东谈主注贪图是一座高达12米、巍然兀立的记挂碑。这里长逝着自青海油田开发以来,因公、因病圆寂的400多名油田员工及家属。
半个多世纪前,来自五湖四海的石油东谈主,构成了一个和谐亲热的团队,是着实酷好酷好上的一家东谈主。他们是战友和工友,濒临恶劣严酷的当然环境,全球抱定一个信念:把地下的矿藏开采出来,给年青的共和国运输动力,尽快摘下穷国弱国落伍国的帽子!干部和工东谈主每天沿途在井场抡大锤、打炮眼,沿途在郊野睡帐篷,沿途啃开裂得像石榴似的大馒头,沿途念念念桑梓的亲东谈主,沿途寻找排遣并立的方式——打篮球、看露天电影,在办事节沿途朗读李季和郭小川的诗篇……
多年后,其中的好多东谈主又不谋而合地长逝在一处。沙漠之上,仿佛上天备好了一张庞大的眠床,全球生前是昆仲姐妹,死后也要亲亲热热地聚在沿途。这里莫得鲜花,莫得常青藤,莫得音乐,果决也不会有大雁或夜莺的传颂,有的仅仅随时会刮起的风,以及四周茫无涯际的荒漠。关连词,躺在这里,便仿佛还能听到石油在地下奔流的声息,依然莫得脱离钻井队和勘测队。
踩着雅丹地貌的残丘,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坟场上,我的鞋子灌进了一把沙砾。我莫得把它们算帐出来,似乎这么不错更深地逼近他们的灵魂,体察柴达木也曾的脸色岁月。
1955岁首冬,由八位女地质队员构成的测量队在冷湖至大柴旦途中进行测量使命。收工后复返时,大风骤起,威望汹汹的黄沙转眼笼罩荒芜,来时的脚印被黄沙掩埋得了无印迹。她们牢牢地抱在沿途取暖,决定扎起帐篷当场露营。在饥饿、干渴与清冷中,八位恰恰芳华妙龄的石油女工长逝在戈壁滩上。
我还记下了墓碑上好多平淡普通的名字,诸如陈自维、张秀珍。这对夫妻是青海油田的第一批勘测队员,在沙漠中相爱,在帐篷里举行婚典。上世纪70年代,他们调往华北油田使命,退休后假寓河北任丘。1981年张秀珍因病离世,留住遗嘱,把骨灰埋在冷湖。几年后丈夫陈自维离世,临终前条件将骨灰送回冷湖与妻子合葬。他们的宅兆被风雨剥蚀,只剩下一小堆沙土,但我能设想戈壁滩上他们甜密的爱情、高涨的芳华。
来自北京的石油众人黄先驯也长逝于此。他屡次发愿要来柴达木锻真金不怕火,却因各样原因未能成行。1980年正准备登程时,他遽然病倒。在病房里,他留住遗嘱,将骨灰埋在冷湖义冢,也算达成了来到冷湖的素愿。
走出墓园,抬眼回望,看到西天巍峨的昆仑山和阿尔金山,山眼下的流沙河时隐时现,夕阳的余光正为山顶镀上一层金边。
阿吉外传
柴达木盆地的石油工东谈主提及阿吉,就像评论一位最熟悉、亲近的家东谈主。阿吉全名为木买努斯·依沙·阿吉,他曾带着驼队做买卖,走南闯北二十几年,被誉为柴达木的“活舆图”。在青海油田开采初期,阿吉老东谈主为寻找石油立下了功标青史。
在位于敦煌市区的青海油田展览馆,我见到了阿吉老东谈主的青铜雕像:他体魄魁岸,长须飘飘,头戴一顶玄色的绒线帽,骑在一匹骆驼上,手指戈壁深处,死后随着几个相似骑骆驼的石油勘测队员。这尊雕刻取材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照相师费龙于1954年拍摄的相片。
当时的阿吉已进宛转顺之年,却不见老态。他像一位游历四方的仙东谈主,骑着骆驼穿越茫茫戈壁,爬峻岭,进沙漠,嘴里哼唱着陈腐的歌谣,渴了喝一口壶里的水或酒,饿了啃一块妻子在土炉里烤制的馕饼,天黑了在郊野当场露营,开阔的笑声从帐篷里传出。石油勘测队的队员王人说:“咱们的阿吉,是神灵派到柴达木传递福祉的信使,是一位在西部大地上行吟的诗东谈主。”
对于阿吉老东谈主作念石油勘测向导的故事,像春季漫天飞翔的蝴蝶一样多不堪数。
勘测队初进柴达木茫无涯际的无东谈主区,莫得公路,更莫得树木算作地标,车轮随时可能堕入沙土或洼地。阿吉风物自由地上前走,频频绕弯,终于踩出一条不错承重的路。此后,他转过身来,把手一挥,车子沿着他的足迹一齐前行。时隔不久,更多的勘测车开进戈壁滩,车灯照亮瀚海。这一条条路,来自阿吉磨破了的脚底板。
戈壁滩上,白日光照锋利,堪称“沙漠之舟”的野骆驼也会渴死。勘测队进驻柴达木,最大的问题是寻找水源。一次,阿吉率领小队踏勘,历经资料跋涉,水喝光了,队员们的嗓子干得冒烟。阿吉在戈壁滩上俯首细细不雅察,时而用手指敲击大地,弯腰谛听,终于在某一处停住,朝地上一指,说:“挖!”队员疑信参半地举起镐头,挖到一米深时,一股净水从沙地里渗了出来,荒漠上响起一派欣慰声。
他把我方多年前的履历和不雅察作念了详备的记录,交给勘测队,此后骑着骆驼带路。在冷湖通往花地沟的一派高下交加的山岗上,阿吉远远地看到地上明慧着油亮的光。他翻身而下,高筒毡靴踏向一块黑石头,他捡起来一嗅,闻到了一股浓郁的油香味。勘测队员把石头带回帐篷,拿锤头砸开,集合油灯的火苗,石渣尽然“吱吱”地毁灭起来。自后,这片矿区由阿吉定名为“开特米里克”。
值得一提的是,阿吉与诗东谈主李季、作者李若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1956年,在玉门油田体验生计的李季听闻阿吉老来得女,便约上在青海油田的李若冰,穿越戈壁荒芜来到老茫崖自流井暗意祝福。阿吉刚刚把家从远方的新疆若羌搬来,住在一个帐篷里。李季与李若冰的到来让阿吉有些不知所措,他急促沏上一壶砖茶,说:“这个小克孜(密斯)还没取名字,两位昆仲给她赐个名字吧!”脸膛黧黑的李季证实注解地一笑,显现一滑白牙,说:“小密斯出身在柴达木盆地,就叫柴达木吧。” 在线三级片
阿吉喜得合不拢嘴,髯毛震恐,连声嘟囔:“呵呵,好,好哩,好着哩!”三个东谈主你一言我一语,临了按照维吾尔族的民风习惯,在小男儿名字的后头加了一个“罕”字,叫“柴达木罕”,意为柴达木花。
名字敲定,一碟油炸花生米、一锅炖羊排和一瓶西北烈酒端上桌,三个东谈主直喝到月上中天——这个夜晚,笑声震颤了土峁上空的星。
《光明日报》(2024年12月13日 15版)亚洲色图
|

